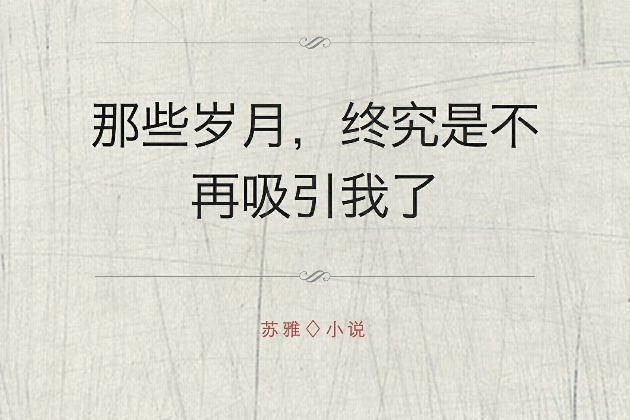
"我可以再爱上你吗?"纪安然要是再年轻几岁,听到这句话之后一定会把手里的这杯Palmer 1989一股脑儿泼到对面西装革履的谷斯年身上,然后愤然离席。
而如今她只是继续细品这杯酒,谷斯年挑出来的酒自是不差,二十多年的老酒,酒色已经泛橙,杯底有着均匀的沉淀,但香气和酒体依然有很好的集中度;典型老酒皮革和动物毛皮的持久香气;嘴中酸度非常清亮,单宁已经基本融化,不过依然小有力道,在后幕支撑得很好,并在后段缓慢延展到幕前。这是老去得工整庄严的波尔多左岸名家风范。
“酒很不错,斯年。”
同在一个行业里,会和谷斯年在葡萄酒大赛里同时作为评委碰面,纪安然不是没有心理准备的。赛后谷斯年特意邀请她来这家湘菜馆子吃饭,又特意备了酒,他的心思她也不是不知道,只是,感情不是,不是你抛弃了又可以捡回来的玩具。
“你喜欢就好。”谷斯年稍松了口气,扶了扶金丝框的眼镜。
一晃五年过去了,这个男人褪去了当初的青涩和局促,本就俊眉朗目,如今愈发的气度不凡,成了样板型的成功老男人,而且还是一个钻石王老五,不知迷倒多少来上他课的小姑娘。可是,纪安然她,已经不是当初的小姑娘了。
“斯年,你不知道,很早以前我就不再喜欢喝老酒了。酒是很不错,可是那些岁月,终究是不再吸引我了。”
…
年轻时她喜欢喝老酒,总觉得经历岁月洗礼的葡萄酒有一种神圣的光芒,褪去鲜活的色彩和喧闹的香气,时间从酒汁里剥落出一块块的沉淀,酿酒教授说,那是掉落的色素和单宁凝聚而成。
安然每次喝老酒就把瓶子里的沉淀都倒出来,大块的拿来尝尝,酸酸的,果然是单宁酸。细小的,就混在杯子里,喝了,觉得酒体就又厚重了些,像年轻的酒。斯年就批评教育她,老酒的酚类物质析出形成沉淀,颜色自然变淡,酒体自然变薄,“人家品老酒品的就是这个淡,你又把它们倒回去,岂不是暴殓天物?”
安然不是不爱老酒的雅淡,“我就是想看看,那些失去的,还能回来不”。
不过是一语成谶。
一起在第戎毕业的时候,谷斯年不去找实习,而是立即开始了他的品酒高级证书的征程。纪安然光看看将生产的那些厚书就咂舌,“咱们修酿酒和田间的时候,学校请了隔壁大学酿酒系的教授们轮番轰炸,短短一个半月的法语集中课程,法国同学都受不了了,你怎么还回去重新自学一遍,还找英语的罪受?”
谷斯年只是用苦读证明了他对这个顶级殿堂证书的需要,留纪安然一人为实习奔波。最后纪安然没能留在勃艮第,去了波尔多,两地分居起来。一个实习工作,万千头绪要理,一个埋头读书,誓要最短时间考下证来。每次电话亦是匆匆,不过每次成绩下来的时候纪安然会接到谷斯年兴奋的电话,“安然,我就差最后一个课就考过了 !“
只是纪安然不敢问,考过了你会来找我吗?她不是不明白这男人把事业放在她之前的心思,纪安然恨的,是谷斯年不声不响的就接受了国内公司的offer,迅速的回国,消失在她面前。
最后的最后,纪安然歇斯底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难道在你心里,我真的有那么不堪吗?”
戴高乐机场的广播音在电话听筒里回响,谷斯年缓缓叹气:“安然,别为了我放弃你自己。”
“谷斯年,你个混蛋!不就是仗着我先爱上了你!”
年少时,我们相爱,以为那就是全部。
…
大上海华灯初上,纪安然仰头看着高楼上流光溢彩的灯,那些年常走进她梦里的谷斯年如今真的坐在了她面前。
“安然,我知道你恨我。”谷斯年的声音依然那样好听,那样好听的声音也曾经说出过那样残忍的话。“当初我逃避,是因为我没有勇气,去给你一段幸福。如今我知道我错了,请你回到我身边,可以吗?”
纪安然把这支老酒瓶底的最后一口倒在自己杯里,轻轻摇了摇,让细密的沉淀浮在酒汁之中,缓缓的喝下。酒体顿时饱满起来,仿佛还增加了一些浓郁的果香,那是Palmer令人称道的浓香。这些曾经让她爱上这支酒的浓香,如今在追忆的味蕾中若隐若现,就像那些曾经轰轰烈烈的爱恋,在模糊的记忆里迅速闪回。良久,酒液入喉,细微的颗粒感轻轻的烙在味蕾深处,那些时间剥落的心伤,也永远的烙上了她的心头、她的味蕾。她已经很久不这样喝老酒了。
因为那些失去的,是再也回不来了。
我不恨你,我只是,不再爱你了。
“斯年,那你来波尔多找我吧。不然,我们就不要再见了吧。”
纪安然多了解谷斯年啊,在他愣神的那一刻,她迅速走出了餐厅。
他到底没有追来。
她坐在回酒店的出租车上,车窗上印着自己的精致妆容。赵若愚的电话从巴黎打来,“怎么样,大赛还顺利吗?”
“若愚,下次你还是陪我来吧。”
“怎么了?”
“没事,就是想你了。”
“安然,你怎么哭了?”
“若愚,我们结婚吧。”
今天我喝了一瓶老酒的最后一口。法国有谚语,喝了瓶底儿的人,年底会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