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迪娅·努斯鲍姆
Katia Nussbaum
Katia Nussbaum是意大利托斯卡纳著名的Brunello di Montalcino产区第一个获得有机认证的酒庄——圣保林诺酒庄(San Polino)的创立者之一,也是生物动力法的积极实践者。她提出我们有必要重新定义二十一世纪的生物动力法。
凝视树木交错的河岸,种类繁多的植物覆盖其上,群鸟鸣于灌木丛中,各式各样的昆虫飞来飞去,蚯蚓在湿土里爬过,仔细想想,这些构造精巧的组合形式,彼此之间是如此相异,却能够以这样复杂的方式相互依存,其实它们都是根据自然法则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这是如此有趣的事情……生命是如此的壮阔…地球依照重力定理绕行太阳,从这么简单的起源,进化出无数最美丽,最奥妙的事物——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节选,185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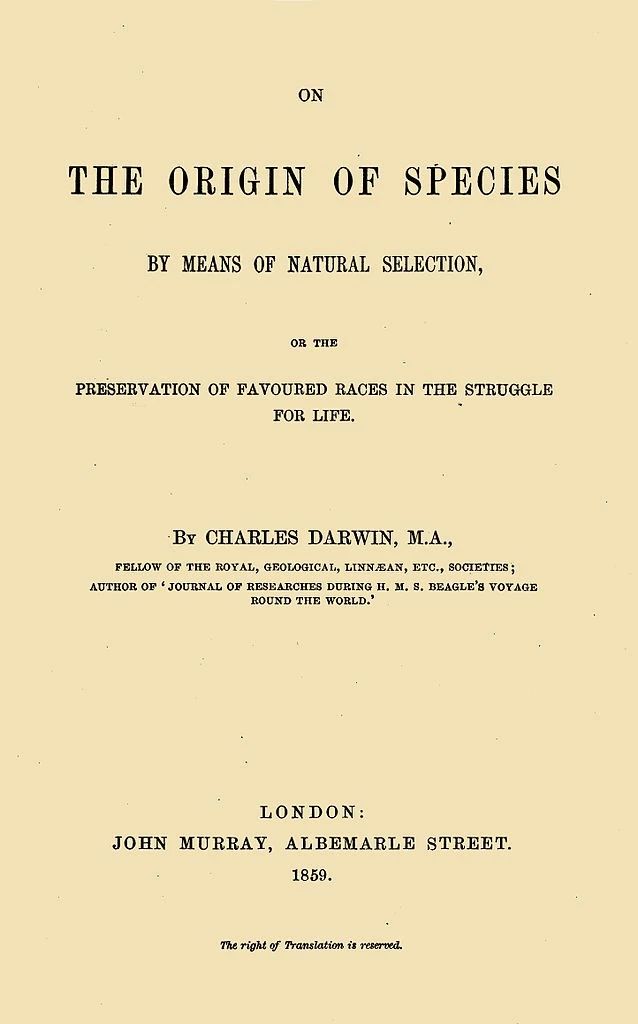
我在这篇短文里阐述的所有观点都来自和托斯卡纳蒙塔奇诺地区的橄榄树及葡萄藤打了30年交道的结果,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大家在阅读了这一系列问题后,对生物动力法有一个现代的、切实的视角,就像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有机葡萄酒酿酒师所看到的那样。
从最初我们在1990年买下那栋古老、破旧但却非常迷人的房子连带五公顷荒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想要酿造一款前所未有的有机红葡萄酒Brunello di Montalcino和一流的橄榄油。
我的丈夫路易吉·法布罗(Luigi Fabbro)在巴西亚马逊丛林里为绘制森林生物多样性地图这个项目工作了很多年。很快他发现生物类型的多样性并不纯粹是偶然性的,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有机体共同作用,从而形成了互利互助的亲密关系。于是他决定把这些理念带回圣保林诺酒庄,用来酿造出能充分体现风土生物多样性的葡萄酒。
我们想做一种纯粹形式的有机农业,在葡萄园里使用微生物代替硫和铜,酿酒时只使用原生酵母。一开始,这种做法让很多人侧目,我们的自尊心也经受着考验。多年以后我可以高兴地宣布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战胜了挑战,酿出了许多精妙的桑娇维塞(Sangiovese)葡萄酒。

但是这个过程并不简单,由于我们的方法很新奇,所以我们必须经常就一些在葡萄种植及酿酒中出现的问题求教于学术界的科学研究,这些经历和其后获得的知识再融汇过去多年我其他的一些想法(农业和哲学方面的)终于使我重新理解了生物动力法的定义。
对于我来说,2016年母亲送给我一本名为《树的秘密生命》(The Hidden Life of Trees,William Collins出版社, 2016年版)的书时,一切终于都变得明朗了。这本书是Peter Wohlleben写的,他是一个护林人,这本书十分精彩,很快就成了国际畅销书。Wohlleben解释说森林里的树木通过深层土里的真菌网络以及信息素互相交流,它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因为树木们需要互相照顾。树木依赖于相邻树木而生存,如果一棵树死了,倒下了,树冠就会出现空隙,阳光照射进来后会烤干森林地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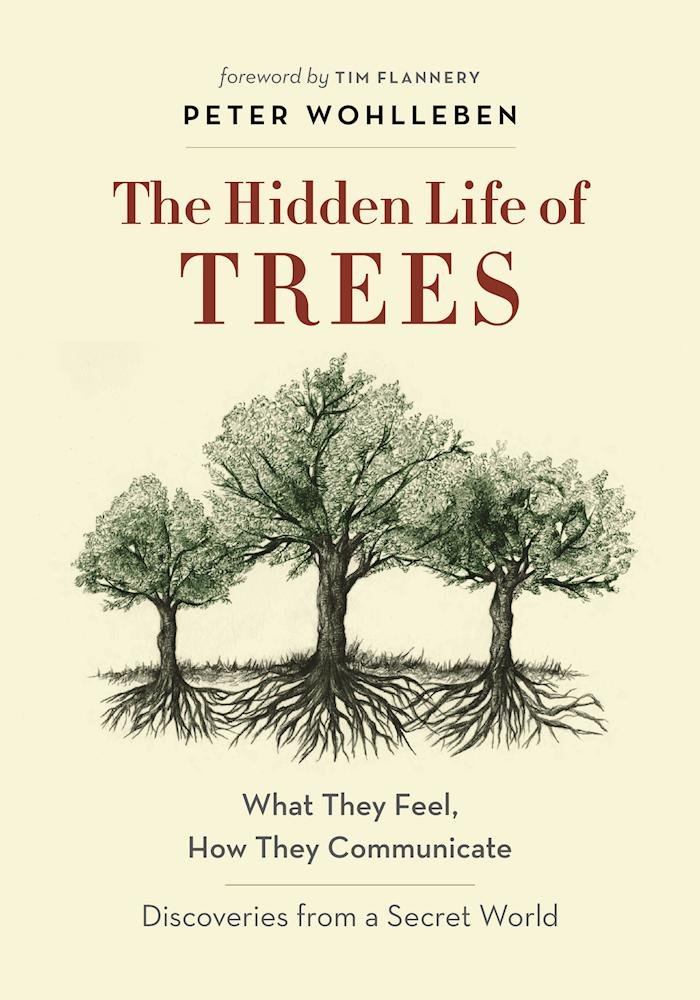
Wohlleben解释了树木是如何抚养小树苗的,还解释说如果一棵树病了,相邻树木会照料它使它重回生机;如果一棵树真的要死了,它会将身上所有的营养都输送回土壤里,以便让周围的树木受益。他的结论是一座森林不只是一些树木偶然地生长在一起,它其实是一个社会。
这个观点让我大开眼界,完全打破了我曾自以为是的认知。我对生命的哲学也产生了怀疑,长期坚持的一些信念瞬间被击垮了。难道说树木是有意识的?我开始认真思索意识是什么,什么东西/人是具有意识的?当然,如果意识的低级形式可以被定义为具有记忆、反应、学习和计划的能力,那么树木是属于有意识的,意大利神经生物学家Stefano Mancuso最近也在他那本非常出色的《植物的革命性天赋》(The Revolutionary Genius of Plants,Atria Books出版社,2017出版)一书中阐述了类似的关于植物意识的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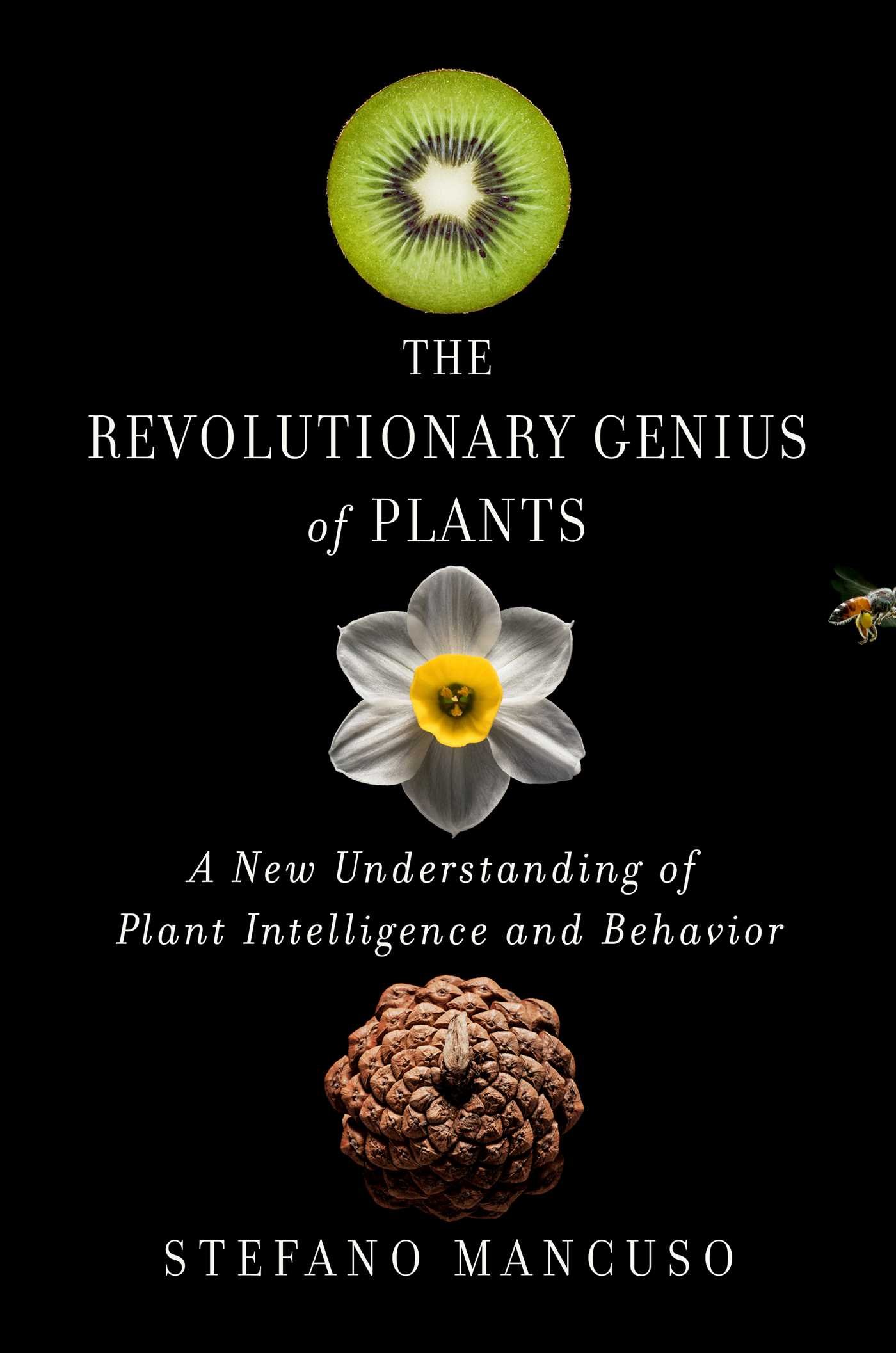
作为一个酿酒师和葡萄种植者,我还有社会人类学文凭,不禁思考着:“这和我们的葡萄园又有哪些关联呢?如果树木是社会存在,那么那些一行行整齐栽种在小山坡上的葡萄藤呢?它们是成千上万个孤独无助的存在吗?”
这么看来它们真的是太可怜了,所以我联系了Primrose Boynton,她曾经和基尔(Kiel)的马克斯·普朗克进化生物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of Evolutionary Biology)合作,她在我们葡萄园里工作了四年,研究圣保林诺酒庄风土里存在的天然酵母的类型和生命周期,发酵过程中酵母在葡萄汁里的数量,还有它们繁殖杂交的能力以及许多其他奇妙的方面。
我只问了她这个问题:你认为我们的葡萄藤是孤独无助的吗?对于我这封苦恼的邮件,她鼓励地回复:“不,恰恰相反。”她告诉我我们的葡萄藤都在愉快地闲聊,我没必要担心。我们的土壤是健康的,而且我们有极其健康的菌根群落。
真菌的秘密生活
菌根菌是有益的真菌,它们和大多数植物的根系共同生长,通过将根系表面积扩大百倍甚至千倍,来提高根系从土壤吸收水分和营养的能力,这些物质被葡萄藤作为食物利用。菌根菌还能释放强有力的酶,帮助分解养分比如有机氮、磷和铁,然后它们会被输送给葡萄藤。
认识到我们的土壤有着健康的菌根群落勾起了我更深入阅读这方面内容的兴趣,我开始思考:如果我们能够加入葡萄藤之间的这种交流,那会怎么样呢?
是否可以向可持续农业的方向更进一步?如果植物们可以交流,警告相邻的植物周围有侵略者,这样它们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比如往叶子/果实里输入更多的单宁,使叶子和果皮变得更苦更硬实,这样它们对于昆虫来说就不再可口,也让真菌和细菌更难以附着。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加入到葡萄藤的交流中使它们自身对侵略者产生更强的抵抗,而不是仅仅按照我们惯例的方式去喷洒微生物,那会怎么样呢?我们在夜间喷洒微生物,因为它们的生长需要更高的湿度。喷洒微生物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葡萄园里的生态空间会充满这些友好的生物体,霜霉菌就没有地方生长了;第二,这些微生物可以吃掉霉菌。
所以能和葡萄藤进行沟通是否在可持续葡萄种植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呢?

自从产生了这些想法后,我有机会和一些涉农产业的人交流,特别是那些研究新的可持续土地/农业管理方法的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研究领域,也是下一步发展可持续农业他们的任务。现在的关键是需要去了解土壤,了解它的构成,里面存在的微生物,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等,这样才可以圆满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我开始研究土壤里的真菌是如何工作的,它们从哪儿来的,它们在干什么。出现的答案却令人困惑,它们不仅在植物之间传递信息,还从深层土壤里汲取大量的营养物质,通过菌根系统输送到葡萄藤根部,以此给葡萄提供养分和水。作为回报,葡萄通过叶子吸收阳光转化为碳水化物再输送给深层土壤里的真菌,使它们能够存活。这是完完全全的互相依存。
自然是竞争的还是合作的?
换个角度,我转而开始研究有关人类生物群落结构的理论。我了解到在我们身体里的每个细胞中,至少携带着10个真菌、细菌、酵母菌或病毒细胞,这个比例至少是一比十!所以我开始思考:“这说明什么?我或者你的内部和外部是什么?我是由什么构成的?”甚至“我是什么,我是谁?”
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开始意识到我们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共栖共生、协同合作的流动世界,所以我为什么总认为自然是竞争性的呢?适者生存难道就意味着弱小的被淘汰?我回过头去再看达尔文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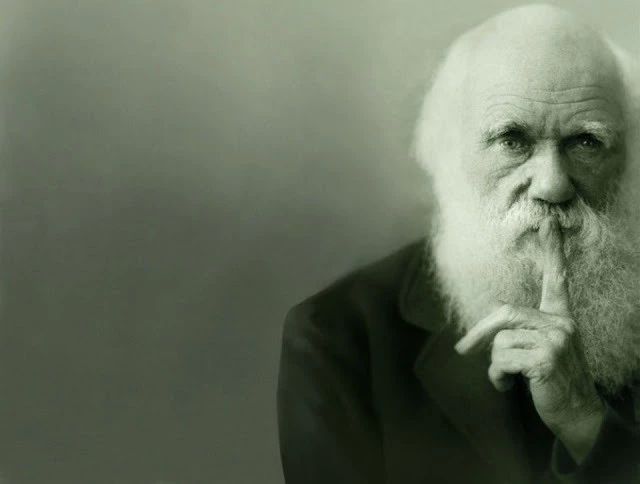
达尔文在1859年创造了“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这一术语,“原则是每一个(生物特征)的微小差异,如果是有利的,就会得以保存。”他的朋友和工作伙伴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更愿意用“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这个词,看起来达尔文只同意在讨论“适应性”的情况下使用这个词,即特定生物适合特定空间和时间里的特定环境。正如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第五版(1866年)中所说,适者生存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更适合于某个紧邻的本地环境”的生物体。
所以“适者生存”= “那些最佳合作者的生存”。
我现在相信“适合(fit)”这个词的语义被严重曲解了。
在工业革命前的英格兰,“适合”(fit)多数情况下是指某件东西适合情况所需,一块正合适的拼图,或者相同力量的东西适配在一起。例如:“那样的举止不合适”,“我的鞋子很合脚”或者“他们是合适的伙伴。”
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时正赶在工业革命之后,万国工业博览会的八年之后,那次博览会展示了现代世界里让人惊叹的缤纷成果。
作为一种经济模式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给新中产阶级带来了财富,殖民主义的残暴(和奴役)所带来的财富也滋养着英格兰工业,这一切需要在道德上获得合理的解释。
作为回答这个问题的权威,宗教可以用加尔文主义宿命论去解释:生命中的财富证明了你就是一个天选之人或者神圣之人,在天堂里定有一席之位。这一理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他1905年发表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里得到了最好的阐述。
通过语义上的细微差错,把“适合”(fit)这个词的意思定义为“身体能力”(physical prowess)而非“合适性”,资本主义散漫的意识形态就可以用“适者生存”的概念进一步让“竞争”获得了合理性。如果自然是竞争性的,那么延伸出去的话,人类本性作为自然世界的忠实反映,也是竞争性的。这样,资本主义作为人类本性的反映就是合理的,可以被视为一种自然现象。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德国纳粹那里得到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在那儿除了高贵的雅利安种族以外的任何人都被消灭了:犹太人、同性恋者、罪犯、残障人士和吉普赛人(还有其他的)。借着对适者生存理论的辩护,一切都被湮没殆尽,所以适者生存的德语翻译为 Überleben der Stärksten——“最强者的生存”并不是巧合而已。
那么这些和葡萄园、酿酒以及葡萄酒又有什么联系呢?
由于我的想法在发展变化,其他问题又冒了出来。如果自然是合作性的而不是竞争性的,那会怎么样?那么该如何看待人类本性呢?又该如何看做一种商业模式呢?
如果自然和文化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如果有关自然的概念就是一种文化建构(culture construct),会怎么样呢?
如果可以将传统的生物分类学扩大范围,把所有的生物体重新定义为在一个流动的宇宙里、一个共生的宇宙里的流体,在这个宇宙里,我们所有人为了生存而被卷入奇奇怪怪的联系中,当我们进化时,我们和其他生物体混合,形成新的物种,从而和它们不可分离,会怎么样呢?就像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在她写的书《共生的行星》(Symbiotic Planet,Basic Books出版社,1999年出版)里所证明的那样——她观察到线粒体带着它自己的DNA,融合到现代人类的身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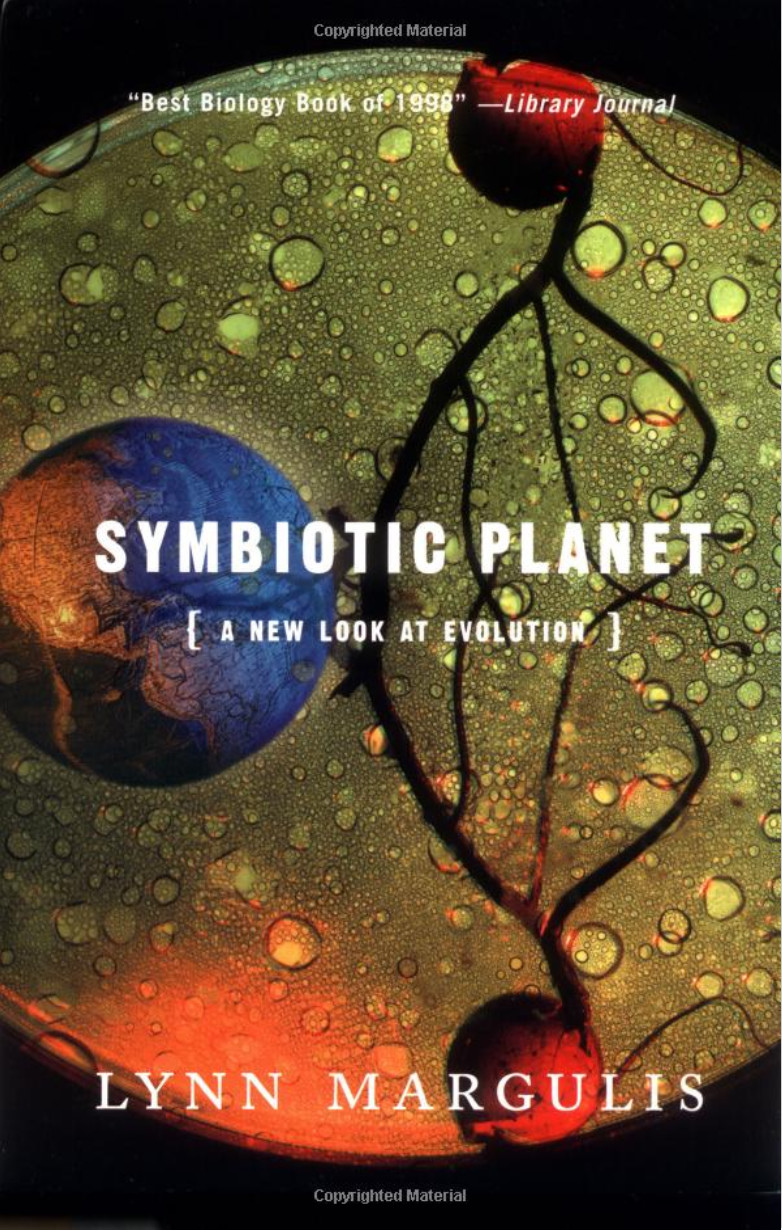
如果我们确实应该重新审查语义范畴,并且认识到我们普遍称呼的“我们和它们”在我们体内是共存的,而正如词汇被灌输了社会政治意义那样,我们重新创造了文化语境和对现实的感受,那会怎么样?如果任何事物都没有本质的真相,我们只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令人愉悦而创造了真相,又会怎么样呢?
生物动力法迫切需要现代化
如果上述任一问题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就该好好反省生物动力法的概念了。我认为生物动力法迫切需要现代化。
将革命性的理念现代化的范例可以在西格蒙·弗洛伊德的理论里找到。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发现了”无意识心理,把压抑视为“(无意识)防御的心理机制”(在1896年发表的《防御型神经精神病》一文里)。从那以后,有关人类的理解就和这个对人类心智的新的理解紧密关联了。
然而,在2019年我们知道他的很多理论因为其父权背景而有失偏颇。女权主义精神病学采用了他的无意识心理概念,考虑到他的人文背景,选择将其学说现代化。大多数女权主义者现在都同意性取向和性别角色可以被视为建构,即具有历史意义的对象。
对于生物动力法我们不能做同样的事情么?
我们可以看到斯坦纳(Rudolf Steiner,奥地利人智学家,生物动力法的提出者) 建构出来的范畴的“真实面目”,其中一些已经超出了使用范围,或者变得无意义了,最糟糕的甚至是反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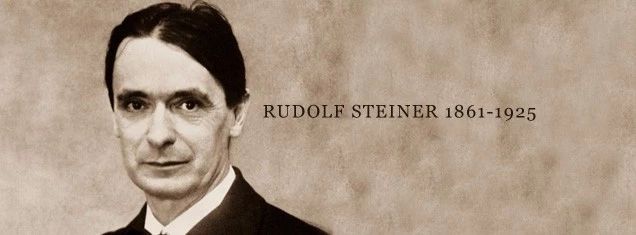
斯坦纳通过极度敏锐的直觉将农场视为一个活的生物体,我们以现代的眼光可以把这看作是地球行星生态系统内稳态的一部分,在以前地球就是盖亚(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斯坦纳的理念在有机运动之前,但却通过运用分析工具和他那个时代和环境的文化阐述出来。他写下这些著作时还没有高倍显微镜,人们也不懂量子物理和弦论,完全是从范畴和基本真相,从二元论概念(例如雄性和雌性),从星象学及隐喻中思考出来的。
现在我们对于植物的交流、生态系统和生物群落、物理、生物、化学、DNA等更多方面都了解的更多,而且我们现在有更好的分析工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斯坦纳那些独创理论的形成和原因,进而以更有效的方式更新实践它们。
我提出如下问题:
- 为什么生物动力法的理论必须固定僵化在斯坦纳最初的作品以及他关于宇宙的理论中?
- 我们能不能不使用他的原始直觉,而把它转化成现代语言,使之对我们更有用,更方便我们理解葡萄藤是怎么运作、怎么和环境互动的,从而更好地了解如何才能培育出更健康的葡萄,酿出更好的葡萄酒?
我相信我们今天可以把斯坦纳所主张的关于生物动力法的新颖而非凡的概念(强调宇宙互相联系的本质)作为强有力的跳板。
当我们重新定义、解释他的那些主要理论,将它们现代化,我们将创造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实践体系,创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一种不那么激烈残酷的商业文明和互利的社会网络。
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具有前瞻性的生物动力法,在其中人不被视为宇宙的模范,不是主宰,而更被视作过去时代的一种社会建构。我们可以理解一个人只是整体的一部分,我们都是被多样化的现实所创造的,同时也在不停地创造着多样化的现实,在这些现实中不再存在基本真相,一切都有可能。
这就是我希望参与其中的新生物动力法。
※ 本文英文原文标题<Biodynamics – new approach needed?>,原文作者为Katia Nussbaum,发布于2019年4月。查看英文原文,请点击此处。本文不代表知味观点。
翻译 | 李萍
校对 | 马云蔚,朱思维,李仪婉
© 知味葡萄酒杂志






